我们先前说到,春物全体故事,可以看做雪之下雪乃在大老师眼中不断从“大公至正”“正面碾压”“无敌”的“真物”一点点褪去光环,一点点变弱,变“伪”的过程。
同时,这个过程对付团子来说,则是她从唯唯诺诺、看人神色、笨头笨脑的“伪物”,变得能够守护朋友,切实地得到“伙伴”的“真物”的过程。
这两个过程都被渡航潜藏在一个又一个事宜的背后,用大老师的自虐和装逼,用同学之间的分分合合和角色酸甜有趣的互动粉饰起来——这正是高明作者的手腕。大老师和雪乃之间心有灵犀的相互挖苦,团子的愉快和委曲,还有平冢静、一色、小町时时送上的搞笑桥段和福利,都牢牢地吸引住了读者的目光,转让航能在障眼法之下布局,在角落里埋下大量致命的炸药。
须知道,高明的作者一定要关键的东西无声无息地潜入读者的内心,却绕过、麻痹读者的知觉,待到揭晓时才让他们震荡、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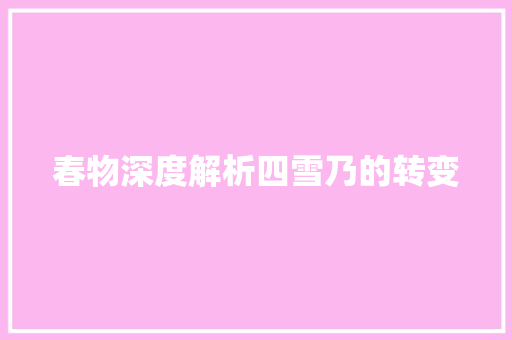
本日,督军我要为各位看官仔细剖析,找出这两个过程的内在机理——为什么雪乃会变弱,团子会变强。
并由此引出对“真物”的第二重阐明。
让我们暂且抛开渡航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晦涩话语,丢开《春物》几个主角之间,回到更古老的,更明晰的王道作品中——
《灼眼的夏娜》《全金属狂潮》以及许多的作品都涌现了如下桥段:
身为冷漠杀手的主角,由于美好和平的日常生活,内心变得温暖。然而在遭遇了真正的强敌时,却受到某些难以言喻的情绪羁绊,难以对抗强暴的对手。
这些仇敌很诧异,由于他们印象中的主角,继而嘲笑主角们“由于和平的生活”,失落去了锐利、果敢——
“很难相信,你便是以前无敌的杀手”
“你现在迟缓犹豫的这副样子真是可笑丑陋”
“堕落了”
“真令人失落望”
而依据作者们所描述的故事,主角也的确因此落入下风,惨遭对方凌辱殴打,自身焦躁不已——且难以理解自己的这种状态。
夏娜在面对玛琼林·朵的时候,相良宗介在上司命令他离开千鸟要,结束和她的任务关系的时候,都呈现出了难以名状的焦躁感。(把稳这里的难以名状,难以理解)
而主角们奋起反击,则是重新找回了自我,振作起来的事情了。
过往的读者和不雅观众们,对付这一故事情节中所蕴含的道理,大多思考勾留在了“恋爱使人懦弱”“羁绊、义务使主角重生”上。读者和不雅观众每每被主角女主之间的相逢、情绪相互确认、昂扬反击所裹挟,在翻滚丰沛的感情之中得到了知足。
督军本日要见告大家:
这个常见情节中蕴含着的真理曾经被我们所忽略,而如今,它是我们解开《春物》的“真物”之谜的钥匙。
为何主角们会先陷入“不可名状”的焦躁?为何因此变弱了?
为何他们末了会找回自我?为何又因此变强了?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要我们能解答这些问题,关于雪乃和团子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主角会陷入“不可名状”的焦躁?!
“炎发灼眼的杀手”的名字中,并不包含与普通少年谈恋爱的部分,成为伟大战士的教诲原来便是夏娜人生的全部、统统,而这教诲中找不到少女的恋爱情绪的“形与名”、找不到词语和说法。当夏娜恼火地创造,男主角悠二的存在是她产生莫名的焦躁的源头时,她试图叨念“我是火雾战士”“我是炎发灼眼的杀手”来平复内心。
夏娜所做的事情,便是用更早之前别人授予自己的“自我”,来牢牢地框定自己,画地为牢,驱逐悠二带给自己的快乐、含羞、紧张,特殊是驱逐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躁感。
督军我这里为大家阐明:焦躁感来源于“炎发灼眼的杀手”“纯粹的火雾战士”遭遇了自己根本无法阐明的、外部的未知东西。这些少年少女之间的暧昧感情,在名为“炎发灼眼的杀手”的“自我”框架中,找不到位置,找不到阐明,理应不存在,可它们却伴随着悠二的存在真实地存在着,不断骚扰着夏娜。
真实存在,却不在原来的“自我”框架之中,无法用先前的“自我”包络阐明的东西在阴郁中律动吼叫,震得主角们心中发慌。
这些奇怪的东西严重地威胁着“自我”的稳定。
这些阴郁中难以名状之物,“尚未有名字的怪物”,被精神剖析学家拉康用“真实”命名的东西,和已经稳固明晰的“自我”之间有毁灭性的张力。
千万不能去触碰,也无法用措辞形容,只是轻微打仗到一点,都会导致“自我”的整体性危急、溃败解体。
(有趣的是,大老师的第一人称有关“真物”自白中清晰地涌现了类似陈述。我这里不列章节,各位感兴趣可以自行探求。渡航的“真物”等一系列观点和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剖析哲学的联系已经摆在纸面上。考虑到他作为传播系专业学生的出身,会摆弄借用这些后现代理论也是情理之中。)
结果正如不雅观众和读者看到的,夏娜本人的战斗意志遭受了内心“无名之兽”的重创,在和马琼林·朵的起初战斗中一败涂地,惨遭羞辱。
(聪明的看官们,看到这里,你们是否遐想到了雪之下雪乃虚弱慌乱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的絮语呢?)
再看《全金属狂潮》
相良宗介,秘银佣兵uruz7的名字,代号,不包含日常校园里酸酸甜甜、充满爆笑和温馨的日常生活。当巨乳御姐上司质问他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想怎么过活时,他说“我就管完成任务”,引来了她的怒火。
此时聪明的毛已经创造了,宗介的“形与名”早已与他生活本色感想熏染到的校园快乐相抵牾了,秘银佣兵URUZ7这个名字中,根本找不到校园生活的“形与名”,无法阐明,而他却负隅顽抗地试图用“我这是完成任务”来进行辩解,来连续“画地为牢”,把自己封去世在原来URUZ7的“形与名”之中。“完成任务”可以暂时地包括保护千鸟,但却容纳不了他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情绪。
其结果,也正如大家所熟知,宗介在被命令撤出任务,和千鸟要分开时,在周围还未有名字却切实存在的甜蜜幸福被撕裂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痛楚和茫然之中。
当他的负隅顽抗以失落败告终,被现实逼得不得不面对这种“自我”与快乐的抵牾时,他就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焦躁。这种焦躁,每每被误读为失落去千鸟的痛楚,然而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夏娜和相良宗介都面对的类似的问题。所不同之处在于,夏娜是没有体会过少年少女之间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具备合法性,乃至她还未认知到其本色。
相良宗介则是在其“完成任务”的佣兵的身份、自我之中,没有公开的律令条文,给与他和千鸟授予有“名分”的关系。他由于实行任务的“形与名”,坚持着这段关系,他也安于如此,自欺欺人地、执拗地假装看不到任务也同样可能结束这段关系,收回“形与名”。当上级下达撤退命令,他和千鸟要的关系、感情就从失落去了“形与名”,从暂时“合法”,重新沦为了“失落去名字的怪物”
综上所述,这些无法用“自我”框架阐明的“尚未得到名字的怪物”“失落去名字的怪物”乃是根本不应存在之物,与名为“炎发灼眼的杀手”“秘银佣兵”的自我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张力,威胁巨大,其涌现对主角意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其结果,作者们也用主角连续吃瘪的事实做了隐喻。
在这些阴郁中的不可名状之物涌现后,完美博识的“自我”就涌现了马脚,开始变得薄弱、虚伪。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春物》中的雪之下雪乃真正面临的问题,和她抵抗、失落败所代表的意义了。
起初,她坚固完美的“自我”能够完美地阐明她所感知到的全部感情。
他人的敌意和恶意。
自己的孤独。
偶尔涌现的伪善者的美意。
每一次她斥责他人的虚伪,每一次她讽刺周围人的造作和懦弱,以及她最铭心镂骨的被抛弃、被背叛,都在加强、支撑着她的外壳。
她没有朋友,也不屑于虚伪的人际关系,她严于律己,也对周围人绝不留情地亮剑,带着报复的快意。
她所切身感想熏染到的内在“真实”痛楚和快意与她为自身订做的“形与名”外壳互相交融,直到两者相互进化匹配到完美合一——这便是《春物》一开始大老师所见识到的完美女神,大公至正的、无敌的、绝不会撒谎的女神雪之下雪乃。
接下来,马脚却涌现了。
大老师、团子的涌现,虽然看似不能改变她无比坚硬完美的外壳,无法改变“形与名”,却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毁坏性影响,他们带来了她所感想熏染到的新的“真实”。
雪乃过去怒斥其他人,遭受其他人冷眼妒忌,遭受背叛,这些情绪已经被整合进了“自我”的框架之中。可是团子不讲道理的美意,大老师满怀期待和赞许的瞩目,还有和她之间的奇妙共鸣,却难以融入到“雪之下雪乃”这个已经坚固无比的“形与名”之中。
阴郁中,不可名状的东西开始涌现了。
正是大老师、团子削弱了雪乃,是他们带来了她“不明白”质问“到底为什么”的,却又是真实的切身的快乐、心伤、冲动、暧昧。
这些融于阴郁、没有名字的怪物让雪乃无法理解、害怕。
由于她“不明白”“为什么”——当她试图回到“大公至正”的自我时,创造这是徒劳的,找不到“答案”。
可她又本能地不排斥、喜好侍奉社给她的体验。随着几个人的关系越来越深厚,融洽,共同的不愿忘却的回顾越来越多,她的原来自我涌现了浩瀚裂口,这些快乐在名为“雪之下雪乃”的“自我”,在她曾经完美的外壳上上割开了大量马脚。
而又正由于雪乃谢绝变动曾经完美的外壳(一半也算大老师强逼、督匆匆她不要改变,好知足自己瞩目女神的欲望,她也乐得因此和大老师保持相互瞩目的知心关系),没能暂时地容许、吸纳这些难以言说之物,因此聚拢在她身上的张力就日渐增强。
这种张力是快乐与自我之间的张力,是“真实”的难以言说之物与话措辞说的道理之间的张力(把稳这一辨别正是大老师第一次哭泣前团子与雪乃交手的点。这一次前后团子与雪乃不雅观点颠倒,且团子完胜了雪乃),是“没有名字的怪物”与“形与名”之间的张力。
而雪乃却认为,“没有名字的怪物”,由于没有名字,以是才是虚伪的,努力否定着切身感想熏染到的“真实”。
但她敌不过。
特殊是在露天过道上抱着团子哭过一场之后,她本色上已经接管了“自我”的败北,不得不苟延残喘地、虚弱地接管这些“不可名状之物”。
而且,彷佛还挺舒畅的。
这标志着雪乃的抵抗走向了尽头,“自我”框架发出散架前咯吱咯吱的响声。在故事里则表示为她快要成为依赖大老师的小女人了。
而且,另一方面,支撑她“形与名”外壳的内在之物,早已悄然地流逝了大半。
她不再整日遭受他人背叛,非议,不再整日负责而义愤地斥责其他人。缺失落了这些内在东西的支撑,完美的、冷若冰霜的雪乃,逐渐连外壳的形状都难以坚持了。
如果说缺失落了“形与名”,却切实存在能觉得到的东西乃是“没有名字的怪物”,那么内在之物早已流逝,缺少支撑的“形与名”则是“衰败的空壳”。
《尼尔:机器纪元》中,“为了人类的荣光”的高尚口号,在厌战感情弥漫于人造人战士之时,就开始衰败。热心和战斗意志业已流逝,那么伟大的叙事、光辉的目标,也将沦为虚伪的空壳,一点一点衰败下去。
“形与名”曾经大概是真实的,乃是由于切身感想熏染到的东西,激情、热心、愤怒、爱恋、痛恨、妒忌,在内部支撑着光鲜亮丽的、充满大道理的“形与名”外壳。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阐述了这个道理:能指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少不了有快感的支撑。普通地讲,便是用饭与主义的关系,用饭支撑着主义。
倘若为了主义,不能用饭,比如为了人类的荣光9S2B不许可谈恋爱,那主义再真也要变成假的,连续坚持主义没人会支持的,人总要恰饭,男女主角总要谈恋爱,这是绕不开的“真实”。
用在雪乃的谈恋爱交朋友与坚持自我之间,如果坚持自我,做自己之后恋爱谈不成朋友做不成,那拉锯挣扎之后,显然还是丢了自我和大老师玩暧昧,和团子搂搂抱抱更“真实”更有有诱惑力)
有内在物支撑的外壳,有切身快乐、痛楚支撑的“形与名”,有快感支撑的意识形态,是“真物”无疑。
当内在的东西先被掏空,无论外壳曾经多么“精确”,都就变得加倍薄弱、衰败——直到彻底沦为“伪物”
“真物”日益沦为“伪物”——这即是玩家透过2B、9S在《尼尔》中看到的空想和意义颓败终焉,也是大老师在雪乃身上看到的令他担忧、心碎的变革。
行文至此,督军我关于雪乃可以做一个暂时总结了。
雪乃最初完美的“形与名”一方面面临了大老师、团子带来的“没有名字的怪物”的冲击,让她曾经骄傲的坚固“自我”试图抵抗,做出阐明,亦或者否定这份快乐,却遭受连续挫败,直至向着这份快乐屈膝降服佩服。
另一方面,和她“形与名”相适配的负面感情、影象逐渐被快乐所更换了,支撑她“形与名”的内容逐渐被掏空了,完美的外壳失落去了支撑,逐渐薄弱、衰败,直到彻底解体。
在“没有名字的怪物”的攻击下,在内在支撑不断流逝的情形下,曾经的冰山美人、无敌的、大公至正、清耿介直的雪乃终极败下阵来,并且虚弱地、无奈地屈膝降服佩服了。
这正是为何雪之下阳乃十分看不惯妹妹后来的样子,“先前就不可爱,很别扭”,可是“现在还不如之前”
雪之下阳乃、母亲的总清算就在路上,少年少女们的暧昧圈子内外危急四伏,连快乐玩耍的叶山、三浦等人都快玩不下去了。
狂风暴雨将至,雪乃此时却“按照大老师希望的”勉强重新拼凑原来的自己,还站在了风口浪尖,搞的毕业舞会即将成为众矢之的——恐怕只能倚仗大老师和团子的拯救了。
这便是《春物》一书直到13卷讲述的雪乃的故事。
同时我们还可以创造,12卷中,大老师明明看到了这些却仍旧鼓励雪乃“规复以前那样子”“连续当女神”的建言,是多么地轻率,多么地自我知足,大概会成为他末了悔的一次行动。雪乃当时显然很不肯意,也很痛楚。由于她自知的完美外壳,她的“形与名”已经犹如俏丽的冰雪般溶解颓败,再也回不去了。
仅剩下的残破外壳,固然还残留着优雅俏丽的形状,却徒具其型,我们很随意马虎看到,她决计不可能抵挡得住母亲所代言的成人间界的横暴冲击。
结尾多说几句,我们也能看到……12卷13卷这个状态的大老师,恐怕也很够呛,呵了个呵……他还抱有天真的抱负,抱有能让统统结束乃至倒退的企图。他自己不来个精神重生,生出个大老师2.0版,光靠投契耍滑,恐怕难以拯救薄弱的、等待他接济的雪乃。
好在,渡航还安排下来了团子这支奇兵。加倍靠近“真物”的团子在11卷一度吓得大老师和雪乃心惊肉跳,逼得他们难以招架,在13卷更有独自出击动摇阳乃大魔王的战绩。故事里团子她反复吃瘪被虐过程中,内在的快乐与酸楚不断大量积累,也即将与最初薄弱的“朋友”“大家”之类的“形与名”完成合一。
督军我认为,雪乃、大老师这两个自命不凡的聪明人,恐怕14卷又要遭重,靠团子来逆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