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读霸班在集体阅读。(资料图)
“读霸”一年借阅543册
一年借阅数百册图书,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最牛读书班”学生朱洁仪,以543册的年借阅量被同学们称为“读书达人”。
朱洁仪来自广东清远,偏爱文史哲和政治学书本。“我特殊喜好中国传统文化,以是文化类书本借阅最多,尤其是许纪霖、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馆藏图书大部分都看了。”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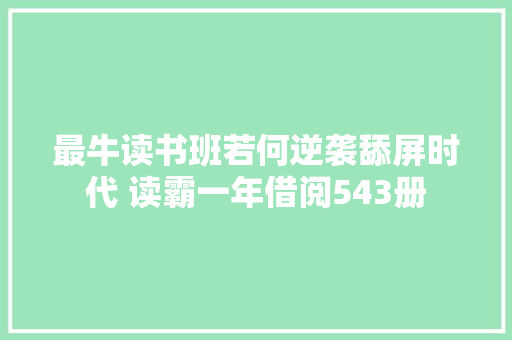
朱洁仪坦言,自己并不是每一本都细读,借书多数是粗读,选取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读,还有一些书是重复借阅的。“如果碰着特殊好的书,我会看得很慢,一天只读几页,摘抄很多内容。”朱洁仪说,读书时还会写读书条记,目前读书条记已有几大本了。
半月谈调查创造,武汉一些高校不乏朱洁仪这样的“读霸”,如武汉大学“借阅之星”王悦年借阅量达653册、华中农业大学的王彬俨197册、武昌理工学院“读书之星”李萍萍102册,但总体来看,爱读书的学生占比不是很大。
梳理干系阅读报告创造,近年来湖北不少高校生均借阅量一贯不到两位数,且呈现低落趋势。武汉大学2015年生均借阅7.6册,华中师大2015年生均借阅7.5册、2016年生均借阅7.1册,华中农业大学2016年生均借阅约为5.5册。
谁引发了他们的阅读激情亲切
现如今,电子阅读越来越便捷,功能越来越强大,“最牛读书班”为何仍旧热衷纸质阅读?在朱洁仪看来,阅读纸质书本能够让心神更宁静。“在手机、pad上的阅读是一种浅阅读,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凌乱无效乃至有害,会影响思维的深度,也会让人形成被动接管的惰性。纸质阅读会让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思考认识更全面、深入、系统化。”
在一个人人手不离机、眼不离屏的年代,如果没有老师的勾引和督匆匆,年轻人是很难坐下来读书的。“最牛读书班”班主任邵彦涛在引发学生阅读激情亲切上功不可没。大一刚进校时,邵彦涛就哀求班上学生每周读3本文史哲类书本,并且哀求做读书条记。
“大学期间思维能力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深度阅读。”为勾引班里学生多读书,邵彦涛曾给他们算过一笔账:一周读3本书,一个月能读12本,4年下来便是500多本书。“每读完一本书,就相称于在自己的知识之树上多挂了一个苹果,那么等大学毕业,你就真是硕果累累了!”此外,邵彦涛还负责批阅学生的读书条记,根据每个人的情形推举书本。
去年一逻辑学生在读完村落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书后,反过来推举给他。“我读完之后,觉得的确写得不错。师生相互推举好书、共享思想盛宴,这无疑是一种传授教化相长。”邵彦涛说。
营造氛围,培养阅读习气
“最牛读书班”学生高学超谈到,3班同学不仅常常在宿舍里互换读过的书本,还在班级微信群、QQ群里分享读书心得,有一种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
班上国际政治专业的孙中一喜好阅读马列原著,他说,这些经典著作思想深刻,论证严密,令人叹服。
一些“95后”大学生内心迷茫,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量课外韶光没有利用好。“他们耽于娱乐,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气,很难静下心来读书。”邵彦涛说,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使一些大学生养成了不独立思考、不深度研究的习气,不利于大学生形成完全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
天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琪昌建言,高校应将“经典阅读”纳入学生培养方案,勾引大学生精确选择阅读内容、增加阅读深度。他建议,高校设立每周一天的读书日,每周分享一本经典书本。(半月谈 俞俭 梁建强 演习王小占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