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有目共睹:一方面是读者的消逝,除了作为批评工具的作家,专业刊物上的批评险些找不到其他读者;另一方面是批评主体的消逝,这不仅是指批评的个性被越来越相似的学术观点和命题所淹没,而且表现为批评家纷纭用写作来证明自己——如今衡量精良批评家的标准,是看他/她是否已转业写文学作品,成为作家显然才是批评家的终极目标。现在的文学批评在读者市场毫无行情,在文学系统编制内则地位尴尬,这些当然使得批评无法赢得作家尊敬。然而这并不源于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懈怠,而是辉煌的“批评世纪”的意外结果,是批评积极融入文学系统编制的结果。当批评与文学系统编制完备融为一体,它忘怀了20世纪之前漫长的不入流前生。
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曾经对作家及文坛形成强大冲击,但经由二十多年的整合与培植,作家协会等文化管理部门,吸纳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培植起以文学奖项为核心的文学系统编制,形成了对作家作品的造就与筛选系统。在这一文学系统编制中,学院批评家成为造就作家作品的润滑油、保护膜,时时与当代作家同行。伴随着新作的问世,从作品研讨会到新书发布会,批评的浸染逐渐从批评变成了背书,能够被作家接管和认同的批评才能成为看得见的批评。批评功能的转变,使得赞颂的角度、深度和新颖性成为批评的追求。在此背景下,批评家的最大声誉是能够登上作家新作的广告页,封面和封底的推举语可以说是当代批评与作家互换的典范。从批评影响看,不是学术论文而是颁奖词,才是当今批评家的代表性作品。宛如浓缩剧集的短视频,颁奖词远比一样平常批评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它的蕴藉阔达、精细隽永,表示了当今批评的最高技艺和水准。颁奖词不仅表示着最精髓精辟的文学不雅观,而且是各种文学奖项隆重推出的批评,是交融了威信性与商业性的批评。然而,颁奖词批评的盛行大概会使得批评者以为节制了文学标准和文坛风向,使批评在一味赞颂中损失了意见意义与判断的自由,更不用说理论创新的积极性。当学院批评渐趋萎靡沉闷,作家的批评因其深谙创作意见意义与技法而成为刊物和网上最受欢迎的批评,精良批评家的创作转向因此既是对作为手艺人的作家的致敬,也是一次次自由亡命。
倘若不是连续抱怨文学批评从文风到作者的不接地气或不及物,实在可以创造文学批评的传统功能即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浸染,在当下已然失落效。当学院批评成为文学系统编制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哀求的批评,读者们自发的批评却遍布网络,微信、豆瓣、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各种APP才是读者们与作家之间的桥梁。新媒体时期动摇的是批评权力机制,当大家都能批评时,批评上网乃至批评家直播并不能改变现状,批评权力的下移必将使得学院批评搁浅在沙滩上。但大概此时的批评才能重归大家发声的“人工”时期,新媒体加持的众声喧哗时期,正是批评最传统、最业余自由的时期。
当放学院批评的创造力紧张表示在对技能革命与文学新类型的关注上。正如二十年前网络文学的呈现吸引大批批评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涌现,AI写作等征象正成为新的文学批评热点,当代批评家都在学习AI技能及干系前沿理论。二十年前熟习的“网络文学会不会闭幕传统文学”的忧虑,也在以新的办法重现。比如有学者著文,指出人工智能写作的涌现意味着网络文学的闭幕,因其背离了网络文学的交互性生产及传播办法。实在人工智能写作哪里仅威胁到网络文学的前景,它甫一壁世就让文学创作身陷危急,谈论人工智能写作是否将闭幕人类文学显然更为急迫。而且从交互性角度,如果将读者与作家的互换视为写作的优秀传统,彷佛也能够创造传统文学的交互性生产语境,只不过互联网的涌现加快了其速率。从写作的技能层面看,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有着平台上的血缘关系,它们在同一个互联网系统内成长,网络文学属于人类在网络蛮荒时期的刀耕火种,而人工智能写作是人类经由了网络工业革命后的日常消遣,后者是前者的技能更新和非中央化播散,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打算机网络的创作潜能,还彻底解放了粉丝们的创造力。从写作、传播与批评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写为难刁难传统文学及系统编制的影响,将远胜于网络文学的影响。在AI的帮助下,写作的特权将进一步扩大到所有人手中,普通人只需口述一段情节,AI就可帮助说话人天生一段影像的时期,快速创作一个文本将成为所有人的权利。网络文学的那些热切催更的粉丝们,在人工智能帮助下,完备可以造诣更为辉煌的文学文本。正如网络文学与游戏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品牌,引领当代艺术的商业化转化和海外传播之路,AI文学也将解放所有人的创造力,造就更多的文学类型与颠覆性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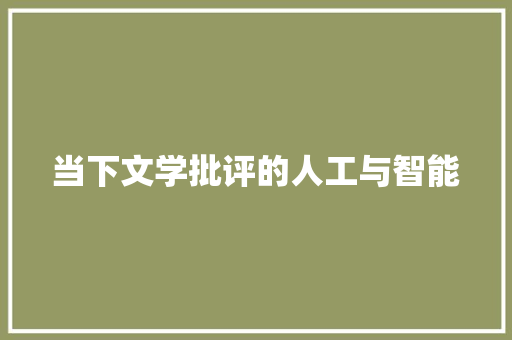
而“智能”时期的批评,首先会改变批评的生产模式与机制。一样平常的批评文章会变得更为廉价,总分构造、内容+艺术、复述情节、辩证不雅观点等会成为AI的标准批评模板,任何读者都可以在AI的帮助下快速天生一篇批评文章。有名批评家也不再须要耗时费力或联名生产批评文章——作家们可以自行生产批评,只须要批评家签署大名。
其次,批评的智能化会催生更多类型的批评与个人艺术家,当商业化批评趋向于批评的建模、数据化与工业化生产,个人化批评会持续探索人类意识、智能机器与艺术生产的联系及转化,批评家与作家的身份不再主要,自由写作实践将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不是艺术家决定人们是否进入三次方天下,而是未来的每个个体都可以将自己智能化并现实化。如果人工智能时期不但意味着机器人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办法加速学习并把人类带入新阶段,而且已发布人类大脑是一个个宛如打算机的认知表征系统,统统理念都来自认知表征系统的运作效果,人性的问题也能在犹如自组织软件系统的意识架构与功能调节中得以解答,那么在感知输入—仿照/学习—表征输出的意义上,人类个体的意识生活和艺术作品将毫无二致。当意识活动与艺术创作有着同样的运作机制,善于写作的作家或批评家无疑是人工智能时期的先行者,如何生活与如何写作/创作将成为同一个问题,节制代码及写作/创作技巧将比考公考研更加主要,成为大家必备的作业。由于创作者才是一个生命的本来面孔,无论她/他是否喜好写作、绘画、看电影、读网文、打游戏等活动,创造活动将成为人工智能时期的生命普遍特色;放弃写作/创作权利才是个人最不幸的经历,无知即意味着被写作而不自知。
当下文学批评正处于智能时期的开端,它的智能化所能带给人们的,大概是刚过去的批评世纪所能展望的真正的批评繁荣:批评的分解既能带光降盆线上呼啸而过的批量论文,知足文学系统编制的须要,也将催生出人机合一的加强型实验艺术家,探索创造的新边界。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符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