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
先从AI实际运用成果的分享开始,目前AI已经在电影行业的各个方面广泛利用,并且技能处于加速迭代过程中。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可能人们过去以为人工智能做出来的东西很机器、有僵硬感,但是现在图像可能比视频技能要更前辈一点,AI天生的图像已经开始有了那种奇妙的感情和神态。我们家有只猫,我让AI给我做一只教授猫,我惊异的不是它能够完成,而且我创造它实在有自己的神韵和神态了,由于至少那只猫涌现往后,晚上有时候一想到猫不是那只真猫,而是被它做出来的教授猫。
尹鸿当然在视频内容上,它还有些毛病。比如群众演员走的画面,用AI呈现还是带有某种机器感。目前AI视频基本上还是更靠近于动画风格的那种,它不能够追求极其逼真的细节表达。不过我以为这些都是技能问题,韶光迟早会把这种机器感肃清到我们难以觉察的程度。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卖力人、中国影视拍照师学会副会长马平:在传统的后期制作流程工艺里面,很多步骤已经在用AIGC替代了。以前可能七八个人的团队要做一个星期韶光,而且一定是充满焦虑的。大家加班之后可能做出一个小样,被导演骂,然后重新做,这是行业的常态。现在,只用一个人半天的韶光,可以替代原来7个人要干7天的事情,98倍的效率。而且不用焦虑,由于他只有一个人跟导演沟通。
在译制方面,AI已经实现了用演员的原声去说天下上任何一种措辞,这能最大程度保留全体角色的完全性。以前我们要不然便是用字幕,但字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视线会不断在字幕和演出之间来回跳切,沉浸感会大大影响;要不然便是用配音,配音实在就跟全体配音团队的能力水平,以及客不雅观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导演,中国科幻家当知识产权同盟理事长图拉古:我们依赖视觉和听觉来感想熏染这个天下,如果我们想让AI超越当前的能力,就不仅仅须要能够对话的AI,我们还须要能够感知和预测的AI,能够做出机器行动的AI。
我和我的团队一贯在做的事情是,让机器像人一样用两个眼睛去识别天下先让打算机像人的大脑一样识别这个天下,虚化掉它,然后再分割它。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的技能可以在绿幕里分割绿色的植物和绿色的衣服的缘故原由,让机器以人类的办法,重新认识和理解天下。紧接着是关于中国企业在AI落地影视行业中的探索和努力,大模型的过度泛滥和人才匮乏是核心难题。尹鸿: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企业很多,但是我们大家都各清闲同样的赛道上冒死地奔驰。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领域将来真正要走到天下前列,须要更多的独角兽,须要更多的行业的折衷,大家不是在同一条赛道跑,而是在不同的赛道上把这个路径拓宽,让大家都有共同的机会。马平:有些统计口径说中文数据在互联网上占不到1%,其余的说大概占20%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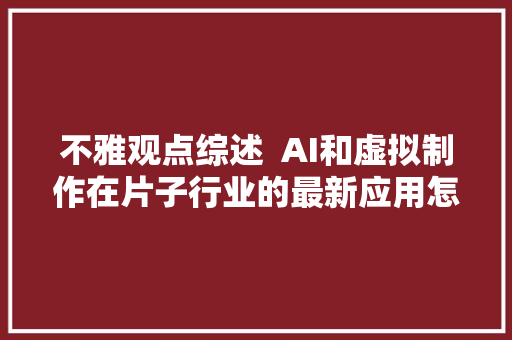
不管是1%还是20%,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文互联网数据相对质量是比较低的,而且大量的网站都是反爬虫机制,以是对数据演习我们处在相对劣势的状态。我们也知道所有西方国家加在一起,供应互联网做事的大模型,加上开源的,两只手就能数过来了,有名的就七八个。但是上个月我们从中心网信办得到的数据,我们备案的向"大众年夜众供应做事的大模型已经有135个了。并不是说数量越多就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本身已经算法相对掉队、算力受到限定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重复培植?由于实在通用大模型它是一个对人类根本知识的理解,这样的一个模型并不须要上百家去做竞争,它实在带来一定的资源摧残浪费蹂躏。对AI真正的需求一定是在家当落地,一定是百业千行。以是我们现在讲垂直模型,如何去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形成一个协力。同样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全体的影视家当特殊是电影行业,客不雅观来说,自主科技发展在前面40多年韶光里面,险些处在一个非常低点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全体电影行业,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有这样的方法论,没有能够系统性地办理一个行业对付科技需求核心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可能须要十年培养,这样的认知和方法论可能须要更长的韶光,这是特殊要关注的问题。中影的义务是,我们现在也在着力去打造一个电影家当的垂直模型。我大略先容一下模式,我们会把全体电影的百口当链,宣扬、制作、发行、放映,以及延伸到后真个文旅家当之中,可以模型化的部分提炼出来,做成神经网络模型。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形成几十个,上百个小模型,这些小模型之间的数据和算法是互通的,从而打造成一个完全的电影家当垂直模型。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希望跟全社会有科技力量的主体,来共同形成一个研发平台,由于它会涉及到的技能不仅仅是信息科技,也有可能会涉及生理学、脑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诸多方面的科学。
把它变成模型之后,它所赋能的不仅仅是影视家当,由于它把电影叙事、电影表达、电影艺术、电影传播所有这些知识履历都变成了算法之后,就可以做事所有做视觉内容创作的人。比如视频博主,也可以用到这样的模型,我们很随意马虎变成线上的SaaS做事,这样就可以打造互助的运用平台,跟全行业去做代价推广。图拉古:除了致力于让AI知晓物理规律和明白空间关系之外,我们还希望机器拥有像人脑一样的最佳功耗比,以45瓦的峰值可以处理非常繁芜的事情。人脑拥有自己的措辞区域、平衡区域、影象区域和视觉区域等等,这些区域终极经由人脑调度决策区域来形玉成部大脑的闭环。机器能否拥有这样的能力,而屏除现在所谓的大模型呢?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把人脑所有的专业卖力视觉区变成专业的垂直AI模型。上边的调度区域换成综合调度决策模型,这便是1991年最早提出的MOE理论,用在网络通信中,现在用在人工智能系统里依然可行。由于我们用实践见告大家,这种联级神经元框架,让AI可以以非常低的算力,就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能力。末了是关于创作者与AI之间的主体性关系,从业者对付被AI取代的惶恐从未完备消逝,但AI依赖过去履历的生产逻辑实质,让从业者对创造力的信心不应该消弭。尹鸿:AI会深刻的影响影视行业,但是它并不能替代我们的影视创作。未来的竞争可能不是如何达到60分的技能层面的竞争,而是60分到100分之间创作层面的竞争,以是制作对大家的制约会减少,但是创作反而会进一步增加。AI的逻辑是从过去的履历中学习,它永久会使得这个作品没有真正的想象力,这种算法路径中,机器很难判断你想要超越数据的欲望。
回眸一笑百魅生,可能人工智能能够做出十魅,但做出百魅是很难做得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悠然是很难表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永久是在新的认知当中去重新感知天下、认知天下、表达天下,人类永久不会勾留在过去的履历当中。而且人工智能的涌现会加速人们履历的更新,由于人工智能永久在学习履历,让你很快站在履历的最前端,以是我们不断的在新的认知根本之上找到情绪表达的办法,超越现实的办法。马克思有一句话说,历史是由人的希望推动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结果是人以为是那样,它就会是那样的。以是历史是力量的无数个四边形的协力创作出来的。换句话说,实在人是无法准确用打算的方法去打算未来的。
马平:很多电影节都在开办AIGC的短片单元。
哪怕现在工具并不完美,并不完善,乃至很简陋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很多很成熟的作品。故意思的是,好的作品背后每每是在校的大学生,而像一些进入专业领域有十来年的有履历的团队的作品,哪怕用了AIGC工具,但制作逻辑还是在传统的工艺逻辑里面。AI大潮的来临,须要在创造力上有更大的解放。先壤影视制作(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周祚:我们所理解的和期盼的AI和大众所认知的可能有不一样的。由于大众在认知AIGC的时候,他们想要的可能是通过输入笔墨或者提示词天生电影的图像,实在这个事情本身对付电影从业者来说,险些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电影的制作流程从来不是一挥而就的,是细分成几十乃至上百、上千个的流程,每个流程都须要有输入,有输出,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是有不同的工种的,发挥人的第一性和主不雅观能动性。这也是全体影像从创作者的脑海里面的一个创想,一贯到到成片的流程。而且这个流程在过去是比较繁芜的,未来只会越来越繁芜,永久不会退回到通过大略输入,经由一个黑盒子变成终极产品的模式。不管我们所说的黑盒子是一个AI算法,还是一个导演的脑袋。在繁芜的工业化体系之下,我们并不须要某些东西来给我们一个整体的办理方案,我们须要的是在我们现在已有的,符合电影工业生产流程的,细分的板块当中,AI可以帮助办理每个板块切实的需求和干系的问题。
虚拟制作
先从虚拟制作对行业提高效率、节省本钱的代价进行展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副研究员,中国影协电影数字制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影协影视基地委员会副秘书长刘藩:近一两年来同行都在讲虚拍,但虚拍和虚拟制作不是一个观点。虚拟制作早几年前已经开始了,虚拟拍摄便是近一两年才开始,而且案例也不足多。说个虚拟制作的案例,2015年旁边乌尔善拍的《寻龙诀》,那会儿同行都在呼吁一个事——后期前置。《寻龙诀》做了一个事便是预演,通过一个大概60分钟旁边的粗糙的动画片,来把《寻龙诀》电影里边的戏都展现了一遍。它能够让拍摄更有效率。前年张吃鱼的《独行月球》也用了预演的办法,更彻底,先拍了一个粗糙的电影,导演跟我说了,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和做了事情节省本钱20%多。深圳市洲明科技株式会社副总裁刘俊:从全体影视工业流程来讲,虚拟拍摄实在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影视内容制作的后期前置,以前是拍完之后,我们再来说做一些殊效,现在是通过UE的引擎,我们先把数字资产做好投放到大屏幕上,再去拍,这样的流程肯定对效率会有提升。第二是它能够节约巨大的制景本钱,没有虚拟拍摄时搭建实景花费数亿元都是常见的情形。它的数字资产积累之后,还可以复用,后期很多同样题材的电影用的时候也可以节约大量本钱。我去年跟郭帆导演互换的时候,《流浪地球1》和《流浪地球2》实在还是用CG去做的。郭帆导演去美国看了之后,他一贯以为AI对未来的数字创作,特殊是虚拟拍摄有一个很大的颠覆。以是未来在全体效率上,通过AI转化数字资产的手段也会有所提升。
针对海内虚拟制作企业商业模式,也有了更为成熟的落地案例。
达瓦影像科技公司创始人卢琪:2024年到现在,我们一共做虚拟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平台的定制,网络电影、院线电影,一共已经做了14部了,但不是全流程虚拟拍摄,大概虚拟拍摄的量是在30%附近。我们公司的棚利用率在90%以上,并且下半年还会开一个更大的虚拟拍摄的棚,由于市场的饱和度确实可以盈利,再去开第二个棚的公司,可能在中国还是没有。商业上的一点启迪是,如果你是一个虚拟拍摄公司的话,你的思想意识上,首先要知道你是为用户做事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的。和任何制片方互助,首先是一个商业行为,不是一个技能行为或技能互换。千万不要跟导演说忘掉你的拍摄习气,千万不要跟制片人说你放弃你的算账逻辑。其余很主要的一点是,环绕这个棚的虚拟拍摄的生态伙伴够不足。比如到永川科技片场,除了虚拟拍摄,还要有基于虚拟拍摄完全的标准化企业,包括器材的、后期的、剪辑的、美术的、道具的等等。
所有东西都完备了,只要给我一个虚拟拍摄场景,我就能把要素配齐,那么按照制片人现有的算账逻辑,最最少没有比以前贵,这个商业互助才会成功。不过,海内企业和好莱坞比较普遍存在标新创新的问题,亟待行业标准的建立。刘俊:虚拟拍摄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从好莱坞开始的。我们很准确地认为中国的虚拟拍摄从去年才刚刚开始,跟好莱坞比可能慢了5年。好莱坞在前面3年LED屏的技能基本上开始已经标准化和固定化了,但是海内会涌现一个情形,你会创造海内的企业特殊喜好标新创新。
比如我们在外洋它的LED显示屏用的DCI2020的标准,但是海内的测试可能就会转向REC的标准。原来环球主流的LED虚拟拍摄间距是P2.6,灯珠跟灯珠的间距是2.6个毫米,但是现在海内开始有1.9、1.85,还有人提出来用1.5。其实在环球都已经被验证了,2.6和2.8是得当的,海内涵这块的追求可能过于标新创新了。卢琪:中国企业的确比较喜好标新创新,比如我要创造一个标准,我要颠覆一个行业,我要改变一个天下,类似于这种话,尤其越在初创期的企业越随意马虎提这些事情,觉得想象空间都很大。像我们达瓦做这些创新和需求的研发平衡,首先我们所有的研发和开拓事情,这两条线都是基于市场需求来的。需求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它该当是通过你一个一个实际的案例和实际的数据统计,然后再剖析出来的。不管是虚拟拍摄,还是虚拟制作,都是导演和制片人和主创团队的工具。能把一个一个的工具做好,形成一个流程,把所有的工具串联起来,实在它便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性的工程,而这种系统性的工程建好了,中国就会有很好的虚拟拍摄团队的涌现。
末了是关于虚拟制作会在未来的电影工业化中充当若何的角色,尤其是在新技能日月牙异的背景下。周祚:最乐不雅观的人认为虚拟制作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电影工业的核心部分,当然这是最乐不雅观的情形。
纵然最悲观的情形,大家也会认为虚拟制作将会在中国电影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模块。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虚拟制作可以切实带来的好处驱动着从业者主动去利用它。比如,以前在我们电影拍摄的现场,有很多不同的层级,如果导演想要把他的思想一级一级地一贯贯彻到片场里最前哨的,摆音响灯杆的人身上,他须要花大量的口舌。但是有了虚拟制作之后,就可以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够看得懂的,并且是非常明确的方法来去肃清信息差,提升你全体创作和制作过程中的效率。以是,不管在未来,虚拟制作能够在工业化流程里面占到多少比重,只要有这一类,对付创作者和制片方存在诱惑的事情,便不妨先推动在全体流程里面更多利用这个技能。至于推动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化流程是不是要环绕虚拟制作来展开,我认为这是后面的事情。该当先推动起来,让大家先参与起来,让工业化流程跑得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