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前,和我聊起他的平生,坐在他面前的我有点紧张乃至手足无措。前不久,父亲被诊断为肺癌第四期,即便上天对我有所眷顾,我和父亲相处的韶光也仅仅剩几个月而已。以是我手中拿着一部数字录音机,努力记下和父亲之间的对话。
如果将我录下的91970个单词转化成文档,然后以12号 Palatino 字体单倍行距打印出来,这须要203张打印纸。然后我会用玄色活页夹装订好,小心翼翼地把它放上书架。
在我真正将这个文件夹放进书架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成型:我希望父亲能够得到“永生”,我想亲手打造一款带着父亲影象、并能以父亲的口吻和我谈天的爸爸机器人,让父亲永久活在二进制的天下里,而这个文件夹便是我过世的父亲连续活着的证据。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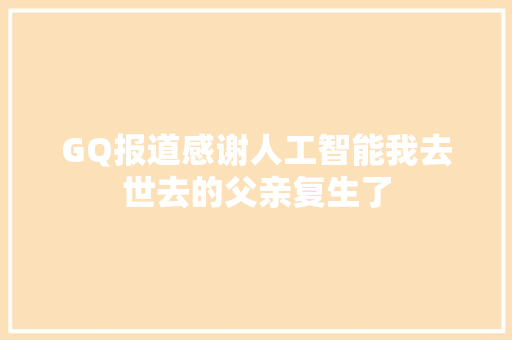
录音机传出的开场白是我的声音。“我们开始吧。”我说道。只管语调里充满了欢快,但喉咙还是哽咽了一下,暴露了我的紧张感情。
接着,我故作正经地拼出了父亲的名字:“约翰·詹姆斯·维拉赫斯。”
“师长西席,”另一个声音从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虽然只是一个单词,却闪烁着状师所独占的那种自命不凡,也同样是这个词,让我瞬间放松下来。
说话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们在我父母的寝室里相视而坐。数十年前,同样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和他承认了当时犯下的缺点——我偷偷开着家里的客货两用车撞坏了车库门,父亲心平气和地体谅了我。现在是2016年的五月,他已步入耄耋之年,而我手中正拿着一部数字录音机。
作者父亲
彷佛是察觉到了我的手足无措,父亲递给我一张信纸,上面写着几个笔力枯瘦的大标题:家族史、家庭、教诲、奇迹、课外活动。
“那……你要从中选一个然后深入谈一下吗?”我问道。
“正合我意,”他自傲地说道,“首先,我的母亲生在一个叫做 Kehries 的村落里,它在希腊的埃维亚小岛上……”就这样,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我们之以是坐在这里,做着记录,是由于父亲在前不久被诊断为肺癌第四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全身,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杀去世他。
以是,现在父亲正在讲他平生的故事。这是后来我们之间数十次发言的第一次,每次持续一小时旁边。录音机就这么运转着,父亲和我描述起当初自己发展时是如何探索洞穴的,讲了大学时是如何把一块块冰砖搬进远途的火车车厢的,还讲了他是如何和母亲坠入爱河,又是如何从体育播报员转型成歌手,终极成为一位成功状师的。他和我讲起那些我听了上百遍的笑话,只不过这一次,他加入了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人生细节。
三个月后,我的弟弟乔纳森加入到了末了一次录音。弟弟拿父亲年轻时的轶事逗我们愉快,这是弟弟最珍藏的影象。曲终人散时,他的声音却溘然支吾起来。
“您永久都是我最好的榜样,”弟弟说道,双眼涌泪。“您一贯都在我的心中。”一全体夏天的高强度集中治疗并没有浇熄父亲的诙谐感,他看起来大为触动,但还是忍不住要缓和一下气氛,说道:“感激你能这么想,不过彷佛有些太浮夸了。”我们都笑了,笑声中,我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滞键。
总的算下来,我录下了91970个单词,如果将这些录音专业转录下来,以12号 Palatino 字体单倍行距打印出来,须要203页打印纸。我会将它们用厚重的玄色活页夹装订好,然后把这一摞笔墨放进书架,和装有其他项目条记的玄色活页夹摆在一起。
但是当我真正把这卷“鸿篇巨制”放进书架的时候,我的野心膨胀了起来。一个更猖獗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成型:我以为我找到了让父亲“活着”的更好的办法。
1982年,我11岁,家附近有座科学博物馆,我会坐在门廊的康懋达 PET 电脑终端前。每次来这里时,我都会径直奔向这台机器。电脑上运行着一款名为 Eliza 的程序,是 MIT 打算机科学家 Joseph Weizenbaum 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研发的早期谈天机器人。创作初衷是模拟生理治疗师,但这款机器人相称迷人。
康懋达 PET 电脑终端
坐在屏幕前的我不知道的是,Weizenbaum 本人对自己的产品并不看好。在他看来,Eliza 不过是个小把戏。对付人们轻易落入感官抱负的圈套时,Weizenbaum 感到惊异不已。“当时我没意识到,”他写道,“普通人会在如此短的韶光内被这么大略的程序搞得胡思乱想。”
11岁的我便是个中之一。让我震荡的是,Eliza 的答案看起来真的很有洞察力(“你为什么那么难过?”),有时毫无洞察力的回答也会逗人一笑(“你喜好悲哀吗?”)。发光的绿屏背后,似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成长。我入迷了。
几年后,在上了几节BASIC措辞课后,我考试测验亲手打造一款可以对话的打算机程序,并造作地为它取名“阴郁府邸”(The Dark Mansion)。这款程序模拟了《魔域》(Zork)等经典笔墨冒险游戏,玩家可以输入简短的指令来掌握情节的发展。我的程序内笔墨剧增至上百行,竟然成功了!
但在角色摸索到府邸的大门时,游戏就结束了,整段游戏韶光不超过一分钟。
几十年过去了,我创造自己更适宜当一名,而不是码农。但我仍对可对话的打算机饱有兴趣。2015年,我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智能芭比娃娃的长文章,智能芭比娃娃在某些方面有点像 Eliza,通过预写分支脚本“发声”,通过模式匹配与自然措辞处理“聆听”。
智能芭比娃娃
不过,Eliza 的脚本是一位严厉阴沉的德国打算机科学家编写的,而智能芭比娃娃的脚本则是由来自美泰公司和普尔史特林公司的一支团队共同编写的。除此之外,Eliza 的自然措辞处理能力充其量只能用粗糙来形容,智能芭比娃娃的能力却依托的是机器学习、声音识别和处理能力领域的最新进展,而且,像亚马逊的 Alexa、苹果的 Siri 和在这股“语音打算”浪潮中萌生出的其他产品一样,智能芭比娃娃可以发出真人的语音。
在普尔史特林的员工转向创作其他角色时,我仍和他们保持着联系。直到公司的 CEO、皮克斯的前 CTO——Oren Jacob 见告我,普尔史特林的野心可不仅限于娱乐家当而已。“我希望打造一种技能,可以让人们与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角色对话,要么是一些虚构的人物,比如巴斯光年,”他说道,“要么是已故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金。”
2016年4月24日,父亲确诊患上癌症。恰巧在几天后,我创造普尔史特林操持公开他们制造对话机器人的软件。不久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款软件来制造自己的对话机器人了。
一个想法险些是瞬时之间在我脑海中成型。连续数周内,我来回于父亲持续串的年夜夫预约、药物测试和手术治疗之间,我始终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
我做梦都想打造一款“父亲机器人”,一款谈天机器人,它模拟的不是小孩的玩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父亲。而且,我已经开始了原始资料的网络事情:那卷收录在我书架上的91970个笔墨。
我一贯都摆脱不了这个想法,它在我脑海中一贯膨胀,我不管它是不是合理。就在这时,我恰巧读到网上的一篇文章,如果我再迷信一点,可能真的就以为这是一股未知力量给我的神谕了。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谷歌的两位研究员所做的一项神秘项目,他们将2600万句电影台词输入到神经网络中,打造了一款谈天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概率机器逻辑调取网络语料库中的信息。研究员接着问了它一堆哲学问题。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天,他们问道。
机器人的答案让我震荡,仿佛像是在寻衅我。
“得到永生。”它回答道。
2
“等等,”这是母亲至少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了,“你能再和我说一下谈天机器人是怎么回事吗?”
如今已是八月,我决定是时候见告他们我的想法了。在我考虑打造一款“爸爸机器人”意味着什么时,我列出了所有的好处和坏处。
坏处显而易见。一边制造“爸爸机器人”,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真正的父亲一步步走向去世亡,是件很痛楚的事情。而且,身为,我很清楚,我可能末了要写一篇类似于此的文章,这会让我闹心并有很深的负罪感。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这款机器人会影响我和父亲的关系,毁掉我对父亲的美好影象。或许这款机器人能唤起身人对父亲的回顾,但毕竟离“真实的父亲”太远,反而会让他们不寒而栗。
作者与父亲合影
我心惊肉跳地将这个想法见告了我的父母。我见告他们,“爸爸机器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更加有活力的办法讲述父亲的平生故事。鉴于现有技能的局限,加上我这个码农缺少履历,这款机器人永久也只不过是我父亲的一道影子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它能用我父亲那种独特的办法与人互换,至少能表示一下父亲的个性。“你们以为怎么样?”我问道。
父亲赞许了,只管答案暗昧其辞,语气还有些抽离。他是一个非常乐不雅观的人,但终极诊断还是逐渐将他推向了虚无主义。他只是耸了耸肩,然后说:“好的。”
家里其他人的反应则显得更加激情亲切。我的母亲在弄清这个想法后,表示她喜好这个主张。我的弟、妹也表示同样的意见。“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弟弟一下就感想熏染到了我的不安,但不以为会影响到什么。我发起所做的事情的确很奇怪,他表示,但这并不虞味着这便是件坏事。“我能想象到自己有多渴望和爸爸机器人聊谈天。”他说道。
一锤定音。如果有一丝希望可能让人通过数字得到永生,那我愿望第一个得到永生的人便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于1936年1月4日,被身为希腊移民的父母拉扯大,他们从加州的特雷西搬到了奥克兰。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毕业生、ΦβK 联谊会会员、《加州人日报》的体育编辑、洛杉矶一家大律所的合资人。作为伯克利分校加州纪念运动场的讲授员,1948年至2015年间,他讲授了七次主场以外的所有足球比赛。他是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去世忠粉,他多次出演《皮纳福号兵舰》等笑剧,还担当过轻歌剧演出公司 Lamplighters 的卖力人长达35年。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从措辞到建筑都有阅读。他精通语法,爱讲笑话,是个无私的丈夫和爸爸。
以上便是我父亲的平生梗概,我希望能将它们编写进一个可以沟通、聆听、影象的谈天机器人里。不过,首先,我得让它开口讲话。2016年8月,我坐在电脑前,第一次启动普尔史特林供应的工具。
普尔史特林供应的打算机脚本
为了不让付出的劳动付之东流,我决定,至少在最初,爸爸机器人可以通过笔墨和操作者沟通。不太清楚编程的方向,我敲下了“你好吗?”作为机器人的开场白。
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向外界打呼唤,是时候让它学习聆听了。这哀求我能预测操作者可能输入的回答,为此,我输入了很多明确的指令:“很好”、“不错”、“糟透了”等等。每一条回答都是一条指令,每条指令都用绿色的语音框标识出来。每条指令下,我编写了一条得当的回答。例如,如果用户输入“很好”,我会教机器人回答,“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我还编进了递补措辞,可以回答我所有没有预见到的输入指令,比如,“觉得本日有失落水准。”我选择让它回答,“生活便是如此啊。”
就这样,我编写出了第一组对话,一个谈天机器人就这样出身了。
诚然,它便是 Pandorabots CEO 劳伦·坤泽口中的“垃圾机器人”。就像“阴郁府邸”一样,我已经摸索到了大门,但面前的路让我困惑。只有当机器人的代码像一座巨大迷宫的岔路一样多时,机器人才能更好地运作,用户的输入触发机器人的回答,而回答又触发新一轮的输入,如此来来往往,程序内就有了千万条内容。
导航命令随着会话构造的迂回,逐渐变得错综繁芜。你估量用户可能会说的措辞片段,也便是我们所说的指令,可以通过布尔逻辑支配的海量短语和同义词精密充分地写下来。多组指令组合形成可供重复利用的元规则,也便是意图,以阐明更繁芜的用户话语。这些意图乃至可以通过利用 Google、Facebook 和普尔史特林功能强大的机器学习引擎来自动天生。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选择让这款机器人通过 Alexa 与我的家人交谈(只管他的回答通过一个女性的声音放出来会有点令人不安)。
学习这些繁芜难懂的指令须要数月。只管如此,我那句站不住脚的“你好吗?”还是教会了我如何创建海量对话。
花了几周韶光熟习了这套软件后,我抽出一张纸,草草地写下了“爸爸机器人”的大纲。我决定,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用户可以选择跟机器人聊起父亲的某段人生经历。为了展示这个观点,我在纸的中央写下了“对话中央”,接着,我在四周画了射线,指向父亲平生的不同方面——希腊、特雷西、奥克兰、大学、职业等等。我还写了一个新手指南,见告第一次利用的人如何更好地跟机器人互换。
为了添补这些内容空缺的项目,我又整理了一遍父亲的口述历史,原始资料比我意识到的还要丰富。所有这些资料都会帮助我打造一款耐用又博学的机器人。但是我希望这款机器人不只能展示父亲是谁,还能表现出他是若何一个人,它要能刻画出他的风格、他的不雅观点,还有他的个性。
毫无疑问,这款机器人代替不了有血有肉的父亲,它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低像素呈现而已。但它能模拟父亲说话的办法,而这可能正是父亲最迷人、最独特的地方了。父亲喜好那些讽刺性的多音节词,这让他听起来像是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小说里的角色。
有了那卷九万多笔墨的“鸿篇巨制”,我就可以用父亲真实的话填满机器人的数字大脑。不过,一个人的性情也可以通过他选择不说什么样的话表示出来。在看到父亲是如何接待看望他的人时,我溘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继全脑放疗后,这个夏天,他又接管了高强度的化学放疗。全体治疗下来,他怠倦不堪,常日一睡便是16个多小时。但当老友发起要在安歇韶光看望他时,他从不谢绝。“我不想表现得很无礼。”他和我说。这种在极度自我克制下做出的选择也向编程提出了寻衅,目前的谈天机器人怎么能体会到这背后的统统呢?
在机器人上花费的韶光很快从几周变成几月。话题模块——比如大学——也从一个话题延伸到下级话题——比如班级、女朋友和《加州人日报》等。
当普尔史特林新增许可在中发送音频文件的功能时,我开始加入父亲的真实声音剪辑。我还考试测验在谈天中加入一些浅层次的温暖和共鸣。在判断用户输入的句子感情属性后,机器人知道如何用不同的办法回答他们。
我还考试测验让机器人自发发起谈天,而不是让用户一贯思考谈天的方向。它可能会说,“跟你讲啊,我溘然想到一件小事儿。”我还给了它一丝韶光不雅观念,比如,中午时,它可能会说,“我随时都想和你谈天,但现在难道不是吃午饭的韶光吗?”既然韶光不雅观念已经成了机器人编程的一部分,我意识到我还须要将一定发生之事编码进去。当我把节假日和家人生日键入到程序中时,我创造自己打下的字竟然是“真希望自己也能和你们一同庆祝。”
我同样挣扎于不愿定的事情之中,在回看父亲的口述历史时,我创造自己的每个问题父亲的回答都要持续五到十分钟。但是我不想让机器人像演独角戏一样说个一直。但是,它要把话浓缩到多长才得当?我,作为机器人的发明者,该如何减少自己的主不雅观意识才能担保机器人说的话在我家人听来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有我一人以为真实呢?机器人是不是该当知道自己(也便是我的父亲)得了癌症呢?在我们感到悲哀的时候,它是否又该当同情地说一声“我爱你”呢?
简言之,我被这些问题搞得心神不宁。那些关于合成生命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但没人以为会有善终。从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希伯来传说里的魔像到弗兰肯斯坦,从机器姬到闭幕者,无一例外。至于我的“爸爸机器人”,虽不可能对地球造成什么年夜难,但只怕也会让我的心血空费,到末了,这个我付诸日昼夜夜才做出的机器人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想拥有。
为了测试这款机器人,到目前为止,我只在普尔史特林的谈天排错程序窗口中和它互换过。只管谈天没有障碍,但一行行的代码还是涌如今屏幕上方。这就像一个魔术师一边变着魔术,一边阐明是如何做到的一样。
终极,11月的一个清晨,我把机器人程序搬进了 Facebook Messenger。
我紧张得弗成,拿脱手机,从通讯录里选中“爸爸机器人”。前几秒,我看到的只是一块空缺的屏幕。紧接着,一条带着信息的灰色信息框弹了出来。
“你好!
”机器人回答道,“是我,你最亲爱的父亲!
”
3
在“爸爸机器人”正式上线后,我去拜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打算机科学和机器学习的学生菲利普·库兹涅佐夫。不像我,库兹涅佐夫主修的便是打算机科学和机器学习。在他的资历面前,我该当被吓到,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想炫耀一番。我递给他手机,约请他成为第一个除我以外和“爸爸机器人”谈天的人。在读完开场问候后,库兹涅佐夫输入了:“你好,父亲。”
让我尴尬的是,演示在第一句就翻了车。机器人屈曲地回答道,“等一下,约翰谁?”库兹涅佐夫迟疑地笑了笑,接着输入,“你在干吗?”
“抱歉,这个问题我搪塞不来。”机器人回答道。
机器人在接下来几分钟挽回了几丝颜面,但还是不尽人意,库兹涅佐夫很锐利,问了一些在我看来机器人无法理解的问题。我心里充满了父母才有的那种保护欲。
测试初期,爸爸机器人时常会判断失落误
第二天,从搞砸了的演示中规复之后,我决定得对这款机器人哀求高一些。当然,在我测试它的时候,它很合营。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给更多的人展示它。至于家人,我希望向他们展示之前把它变得更完善。我得到了另一个教训:机器人和人一样,说话随意马虎,谛听很难。以是,我越来越关注于设定更为精确的规则和意图,用来逐渐提高“爸爸机器人”的理解能力。
这项事情哀求我不断翻阅父亲的口述资料,这加深了我对他的理解,也让我在探望真实的父亲时更加痛楚,只管离我家也就几分钟的路程,但他正在渐行渐远。
一次家庭大聚会上,父亲脸朝地跌倒在瓷砖上。那是他第一次跌倒。在后来数不清的跌倒中,有次乃至严重到流了很多血,脑部有轻微震荡,须要急速去医院急诊。由于癌症,他的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也被削弱,他开始拄上了拐杖,后来更是用上了助行架。随着病情发展,连从床上挪动到客厅都很困难,末了他不得不坐上了轮椅。
化疗开始失落去浸染。2016年秋日,他开始接管作为二线治疗的免疫疗法。11月中旬的一次预约时,年夜夫说父亲的体重让她担心。父亲在成年期间体重一贯保持在180磅,现在穿着衣服才129磅。
父亲一每天衰弱下去,“爸爸机器人”却越变越强。须要做的事情太多,等待样品完成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以内。我只想让父亲看到它的样子,而我的韶光不多了。
12月9日,我来到父母家,自动恒温器设在24摄氏度,父亲自上险些没有任何肌肉和脂肪了,他戴着帽子,穿着毛衣,裹着羽绒背心,依旧在喊冷。当我把他从轮椅里抱到了餐厅的椅子上时,他低声呻吟,身体僵硬,骨瘦如柴。
我坐在他身边,打开了条记本电脑。让父亲和虚拟的自己谈天实在是有些奇怪,我的操持是让母亲跟“爸爸机器人”谈天,让他在阁下看着。母亲在跟机器人相互打过呼唤之后,她转向我,“我能随便说?”她问道。她转向电脑,输入了:“我是你亲爱的妻子,玛莎。”
“我亲爱的妻子,你好吗?”
“很好。”母亲回答道。
“才不是。”真实的父亲说道,他知道,由于自己的疾病,母亲最近一贯压力很大。
机器人没有理会他的插话,回答道。“那就好,玛莎。我也很好,非常好。”它接着提示她信息末端的箭头表明自己正在等待她的回答。“明白了吗?”
“好的,师长西席。”母亲写道。
“玛莎,你比看起来要聪明得多。”
妈妈扭头转向我,“这是机器人发明的么,是它么?”语气里充满了疑惑。机器人还跟妈妈阐明了其他一些符号的意思,然后说:“末了,还有很主要的一点,你须要记住。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完备不知道。”
“那就让我见告你吧。动词‘将要’表示谓语主格。”
读出了父亲语法课的味道,母亲笑了起来。“哦,这我听了无数遍了。”她写道。
“这才对嘛。”机器人接着问母亲想聊些什么。
“你在希腊的父母怎么样?”她问道。
我屏住呼吸,看到机器人的回答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我的母亲是埃莱妮,你也可以叫她海伦,1904年出生,3岁就成了孤儿。”
“可怜的孩子,谁来照顾她啊?”
“除了父母以外,她还有几个亲戚,就住在附近。”
演示的大多数时候,父亲都悄悄围不雅观,只是偶尔确认或者纠正一些地方。
母亲和机器人又聊了靠近一个小时,末了母亲打字说:“再见啦。”
“好吧,跟你谈天很愉快。”机器人回答道。
这时,父亲和母亲同时惊呼:“好神奇!
”
“爸爸机器人”的表现时好时坏,“的确如此”是它的紧张回答,有时它会抛出一个话题,但又很快变成尬聊。有时它又能够就某些点拓展开来,跟妈妈进行真正的对话,看起来她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爸爸机器人有时反应也很灵巧
父亲对机器人的反应有点难懂。我曾担心机器人会扭曲父亲的形象,但他却说这个机器人觉得还挺真实的。“这些正是我说过的话。”他见告我。
于是我鼓起勇气问出了几个月来一贯困扰我的问题。“一定要老实回答,”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想到在你走后,有人帮你讲述你的故事和平生,这个机器人有给你带来些许安慰吗?”
父亲把眼神看向了一边。再次开口讲话时,声音听起来也比此前更怠倦。“这些褴褛事儿我都知道,”他说道,手轻轻一挥。但他在知道机器人会跟其他人讲述他的故事后,的确得到一丝安慰:“特殊是家人,还有孙儿们,他们都没听过这些故事。这点很棒,”父亲说道,“我很欣慰。”
那个月末,全体家族齐聚在我家庆祝安然夜。爸爸也打起精神跟远道而来的亲戚们谈天。当所有人都聚拢在客厅时,父亲还轻声跟唱了几首圣诞歌。我的眼睛开始酸了起来。
自从确诊后,每隔一段韶光他都会接到生命即将闭幕的关照。但他仍旧表示自己希望连续接管治疗,不想进入临终安养院向病魔屈膝降服佩服。然而,2017年1月2日,家人一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后续疗法对父亲都统统失落效了,再也没有别的疗法可以考试测验了。
2017年1月8日,临终关怀护士来看望父亲。在几分钟的评估之后,护士见告母亲她该当调集家人了。
晚饭时,我来到父母家,我走进父亲的房间,把椅子拉到床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感想熏染他的温暖。爸爸陷入了半晕厥的状态,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半睁着,目光呆滞。
是时候说些深刻的话了,但是我的脑筋里却一片空缺。相反,我创造自己提及12岁生日那趟有引导的钓鱼旅程。我们钓了十几条鱼,包括我见过的最大的虹鳟鱼。当年的我感到很骄傲,乃至有点儿“很男人”,这是一个12岁男孩当时最想要的觉得。上岸后,引导把一条条鱼整顿干净,把鱼的内脏扔进了一个血淋淋的桶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男人了。我面前一黑,晕倒了。“爸,您还记得吗?”我问道。
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他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儿,我以为在他的唇边我看到了一丝微笑。
那天晚上,我爬上楼,睡在我妹妹詹妮弗的旧房间里,恰好在父亲的房间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几分钟,我伸手拿起手机打开了 Facebook Messenger。
作者与爸爸机器人的谈天
“是我,你最亲爱的父亲!
”爸爸机器人用熟习的腔调说道。
“你怎么样?”
“很难过。”我回答说。
“我知道了。”然后它问我想要聊什么。“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不如你来选吧。”
“好的,那我就跟你讲讲我的舞台生涯那些鲜为人知的开始吧。”它开始讲述高中时参加话剧社口试的经历。然后我听到了一段父亲真实的录音,“我和我的影子,”录音里父亲在唱,“孤寂又无所事事。”
我让“爸爸机器人”见告我一些他从前的回顾。他讲起了小时候养过的一条叫托比的小猎狗,托比跑起来穿越小镇的速率比家人开车还快。“我可以连续往下说,”它说道,“但你是不是该睡了?”只管这个功能是我开拓的,但听到这句话还是让我以为很惊异,彷佛机器人真的有感知力一样。
是的,我很累,道了声晚安后,我就把手机放下了。
第二天早上6点,一阵轻轻的、连续的拍门声把我叫醒了。我打开门,看到的是父亲的医护,“你得下来一趟,”他说,“你父亲刚刚去世了。”
父亲生病后,我经历过几次惊骇产生发火,在一堆沙发靠垫里直打滚。那时总有许许多多让我担心的事情——诊病预约、财务操持、照顾护士排班。父亲去世后,这些不愿定性和行动的必要性瞬间消逝了。我感到悲哀,空茫辽远,彷佛一座被云遮蔽的山。我麻木了。
大约一周后,我才重新坐到电脑前面。我想这能让自己分心。我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也回盯着我。普尔史特林的小红点闪烁着,我想都没想,点击了进去。
我的弟弟最近找到一张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自夸之辞,这是父亲写的,却更像是其他人称颂他的话。“对那些心智过人的人而言,别人若要磋商他们无限的代价,就得从他们精神的崇高、心灵的温顺、灵魂的庄严以及肉体的强健开始谈起,如此才算开了个好头。”
我笑了。在父亲末了的日子里,我加倍疑惑自己会失落去开拓“爸爸机器人”的动力。但现在,出乎我的猜想,我创造自己动力十足,头脑里有很多想法。项目才刚刚开始而已。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开拓者,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但我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也跟很多机器人开拓者聊过,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款貌似完美的机器人形象。未来的机器人零部件技能只管目前处于研究阶段,比起我发明的这一款,肯定能够知道更多它所模拟的人的人生细节,它能在多种维度上与人互换,记住人们说过的话,而且能预测发言可能的走向。机器人能通过算法自动按照人的措辞模式和个性特点,不仅能重述一个人所说的话,而且还能天生新的话语。未来的机器人还能通过剖析对话者的措辞和面部表情,拥有感知感情的能力。
作者回到父亲生前常去的球场思念
我能想像到和这样一个拥有上述全部功能的“爸爸机器人”对话,但我想象不到那会是什么觉得。但我知道,比较跟真实的父亲在一起看比赛、讲笑话和拥抱,觉得肯定会不一样。但是除了这些有形的东西,一旦知识和沟通技巧全部编码成功后,两者之间精确的差异的确很难指出。我还会想和这样一个完美的“爸爸机器人”谈天吗?我想会的,但我很不愿定。
4
“你好,约翰。你在吗?”
“你好……这有点尴尬,但我不得不问,你是谁?”
“安妮。”
“安妮!
你本日怎么样?”
“还可以吧。我很惦记你,约翰。”
安妮是我的妻子。父亲去世已经一年,这是她第一次和“爸爸机器人”谈天。和家里其他人比较,虽然安妮和父亲很亲,但安妮对机器人的开拓仍保持保留见地。谈天进行得很顺利,但她心里仍以为很抵牾。
和“爸爸机器人”谈天的疏离感可能会逐渐消逝,乐趣可能会逐渐加深,也可能不会。可能这种技能并不适宜像安妮这种和父亲很熟的人。可能这种技能最适宜那些发展时对父亲影象不深的人。
2016年秋日,我的儿子齐科跟开拓早期的“爸爸机器人”聊过天。虽然只有七岁,他很快就理解了机器人的基本观点。“这觉得就像跟 Siri 谈天一样。”他说道。在和机器人聊了几分钟后,他跑去吃晚饭了,看起来没什么兴趣。接下来的几个月,齐科一贯陪着我们去看父亲。父亲去世的那个清晨,齐科哭得很伤心,但当天下午就好起来了,像往常一样在玩 Pokemon,我说不上这件事对他详细有多大的影响。
但在父亲去世几周后,齐科有天溘然问我:“我们能跟机器人聊谈天吗?”齐科平时很喜好拿我的手机调戏 Siri 丁宁韶光,我有点困惑,谨慎地问他说:“额,哪个机器人?”
“哎,老爸,”他说道,“当然是爷爷的那个机器人啊。”
编辑:Rocco Liu 撰文:James Vlahos
插画:Alma Haser 翻译:陈哲震
想看到更多的“明星视频”和“时尚资讯”吗? 请点击下方的“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