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人工智能(AI)的发展已开启加速度,如果人类未来能够通过AI得到自己想学的任何知识,得到不逊于在传统教诲中的体验,那么大学该怎么办?大学会被AI颠覆吗?
在这场由北京大学未来教诲管理研究中央主理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辩论了整整一天。在他们看来,当前社会,教诲的改变、教诲事情者的改变已经迫不及待。
来不及学也来不及教,AI冲击教诲尤甚
爱因斯坦曾说,所谓教诲,便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的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以是教诲的实质,不是通报“显性的知识”,而是增加爱因斯坦所说的那些“剩下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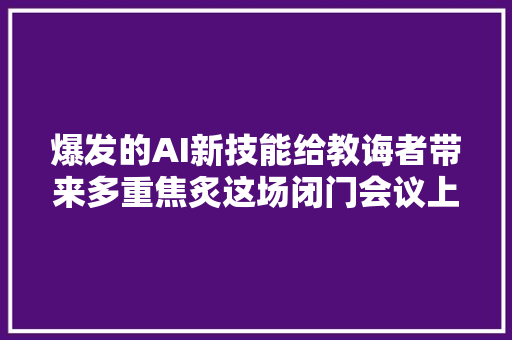
在研讨会最开始,北京大学未来教诲管理研究中央创始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就直陈他的困惑:一个人终其生平,能节制的知识只有AI的百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随着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通过“自学”,在节制更多知识后,那些“剩下的东西”是不是会比人类更多?彼时,我们对教诲的定义还有代价吗?
和林建华不同,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家当研究院院长漆远坦言,他正被“双重焦虑”困扰着。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率之快,让他这位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连最新揭橥的论文都来不及“追”,他半开玩笑地说,由于要学的新内容太多了,“现在都要靠AI替我总结论文概要。”事实上,每一个从事AI研究的学者,过去两年都“压力山大”。
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教授,漆远也承受着“身份焦虑”:在传统师生关系中,老师每每是知识的供给侧;而随着技能的发展,AI今后完备可以承担知识供给的功能,补充信息的鸿沟。“未来,我们究竟须要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老师?”
北京大学理学部副主任、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高毅勤也有类似感触。“过去,大学西席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是教给学生20年后还有用的知识或者能力;但现在科技快速发展,我们不由思考,自己教给学生的知识,是不是在他们还没走出校门时,就已经由期作废了。”
作为大模型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漆远深知,技能发展从来都是非线性的,当积累到某个关键韶光点,就会涌现爆发式增长。而AI目前显然已超越了这个韶光点,正处在爆发阶段。尤其是在ChatGPT问世后,不论外界哀求人工智能有效加速、还是实现代价对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AI现在的升级迭代已经根本停不下来了,这将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形态带来巨大改变。“作为教诲者,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教诲?”漆远发问。
人与天下的交互办法,正因AI而变
犹记得10多年前,在线教诲起飞时,学界同样担心:在线教诲会不会取代线下教诲。但事实证明,再好的技能也无法取代教室上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互换。
但这次,情形并不一样。AI发展带来的是人类与天下交互办法的改变,而这是教诲中尤其主要的环节。那么,大学是否还会对受教诲者构成吸引力?实在,这不仅是中国大学的担忧,不少国外高校也有着同样的担忧。
漆远在思考的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电影《HER》。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人由于每天和手机对话,感到手机比天下上任何人都更懂他,从而爱上手机的故事。漆远说:“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老师、学生或我们中的任何人呢?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碰着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懂自己的AI,这个时候,教诲该当如何变革?”
实在,这些关于未来的设想并不迢遥。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教授说,他有一回在等飞机时,想着为临床医学的学生编写案例库。由于是临时起意,他决定向手机上的人工智能软件提问:“编写一个梗阻性黄疸壶腹周癌的病例,并附上化验指标和医学影像学检讨的结果。”很快,一个完全的病例就涌如今他的手机上。随后,他哀求软件列出病例中的知识点,同样,他很快得到了却果,并且,软件还画出了知识图谱。
王维民不由感叹,有了AI助手,这些事情的完成度不仅很高,而且速率还很快。“在这样的情形下,医学生只要学会提问,就能够通过人工智能节制同样的知识了。”
要积极拥抱AI,也要戒备技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AI的兴起将对教诲等各行业领域产生冲击。梳理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的“焦虑点”,不外乎两个问题:将来社会须要什么样的人?本日的师生如何借助AI更有效地学习?
眼下,不少高校已开始考试测验在传授教化和科研中纳入人工智能干系内容,希望能够增加学生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节制。目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都已将AI干系的课程纳入通识教诲之中。
“当知识生产办法从精英走向大众,大学正逐步失落去对知识的垄断,唯有打开边界、成为创新资源的中央,才能顺应后当代大学的发展趋势。”在林建华看来,AI虽然可以节制大量人难以企及的公共知识,却无法像人一样与物质天下发生联系,认识和改造天下并独立进化。因此,林建华建议要将AI视为工具,积极拥抱AI。大学则应以此培植均衡高效的学习环境,并关注新兴技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戒备潜在风险。
王维民以医学教诲谈道,AI不论是在“总结”病例,还是在节制既有的医学知识方面,都有着超乎人类想象的能力,但就医学教诲而言,当下更该当思考,如何给学生知识之外的东西。在王维民的专家门诊上,他每每一上午可以看30个病人,个中不少病人实在并不须要大动兵戈的治疗,只想和年夜夫聊聊。医患之间的融洽沟通,本身也是一种“治疗”,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让患者安心。“这便是医学教诲要教给学生的。虽然医学知识是必需的,但年夜夫和病人的互换,至少目前AI无法教给学生。”
漆远说,就目前而言,家当界的算力、数据、投入和人才确实走在了高校前面。在此情形下,高校如何做好传授教化、科研,确实是非常大的寻衅。“如果说400多年前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让人类更精准地看到了宇宙、星星,那么本日对科研事情者来说,人工智能便是新时期的望远镜或者显微镜,能够让人类看得更远、看到更微不雅观的天下,而真正的寻衅在于,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它。”